作者:黄琳娜
临床研究发现,流感病毒相关侵袭性肺曲霉病(IAPA)与新型冠状病毒相关侵袭性肺曲霉病(CAPA)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宿主/危险因素、病毒致病机制、侵袭性气管支气管炎发生率、诊断时间、GM阳性率、继发感染率及病死率等方面。流感病毒和新冠病毒的致病机制存在差异是临床表现差异的根本。但总体而言,病毒破坏宿主抗真菌免疫都分为三个层次:第1层,气道上皮屏障破坏,阻碍了纤毛对曲霉分生孢子的清除,进而导致菌丝侵入组织;第2层,吞噬溶酶体杀伤分生孢子受阻;第3层,中性粒细胞对菌丝杀伤能力减弱。IAPA的发病机制主要为肺泡巨噬细胞和中性粒细胞NADPH氧化酶依赖性活性氧(ROS)产生抑制,导致巨噬细胞中LC3相关吞噬(LAP)作用减弱,曲霉吞噬消除也随之减弱。CAPA的发病机制主要为Ⅰ型和Ⅲ型IFN反应减弱,进而削弱中性粒细胞对烟曲霉的杀伤作用。此外,IAPA和CAPA的发病可能都会受到某些药物的影响。对于IAPA,临床普遍使用的抗流感病毒药物—神经氨酸酶抑制剂(NAIs)已经被证实会损害人单核细胞杀伤曲霉的能力。所以,NAIs也可能是IAPA的高危因素之一。而CAPA患者常会应用糖皮质激素及IL-6受体阻滞剂或JAK抑制剂等,可能是CAPA的高危因素。致病机制的差异导致了疾病严重程度的不同。尽管IAPA与CAPA之间具有一些不可变的共同因素,诸如:宿主基因多态性、欧洲癌症研究与治疗组织/真菌病研究组教育研究协会(the European Organization for Research and Treatment of Cancer/the Mycoses Study Group Education and Research Consortium,EORTC/MSGERC)提出的宿主因素、细胞因子风暴、淋巴细胞减低、糖皮质激素。但二者之间也存在明显的不同:流感病毒对呼吸道上皮的溶解作用更强,对ROS产生抑制,治疗使用NAIs,这些因素都可能使流感病毒导致的组织损伤更重,并且更早突破血管受侵阈值,更容易发生血管侵袭性IPA。而新冠病毒对呼吸道上皮的溶解作用较轻,对宿主真菌防御途径的打击也比较轻微,所以,新冠病毒对组织损伤相对较轻,也相对难以突破血管受侵阈值。但在重症COVID-19患者中,除糖皮质激素之外的抗炎治疗(例如:IL-6单抗)应用较为普遍,在强效抗炎治疗的作用下,可能也会使曲霉突破血管受侵阈值,发生血管侵袭性IPA。总之,流感病毒继发IPA的组织损伤可能较新冠病毒更严重。图1是CAPA患者呼吸道的病理表现,A为溃疡伴坏死炎性碎片和分离曲霉菌丝(黑色;原始放大×40)。菌丝位于表面,无血管浸润的证据。B为真菌菌丝侵入组织,与曲霉(原始放大×200)一致。图2是IAPA患者呼吸道的病理表现。A为广泛的溃疡和坏死,存在多个曲霉菌丝(黑色;原始放大×40);菌丝浸润气管黏膜下层。除菌丝侵入性生长外,烟曲霉囊也在气管管腔中被发现(便于产孢),气管上皮细胞上可见分生曲霉。B为曲霉菌丝侵入气管动脉并形成血栓(原始放大×100)。
图2 IAPA患者呼吸道病理表现
IAPA起病急,其起病时间早于CAPA。笔者团队研究发现,IAPA一般在入ICU后48小时内起病,而CAPA通常在入ICU后6~8天(>72小时)起病。COVID-19病程早期病毒直接导致肺泡上皮屏障损伤,纤毛清除能力降低,病程中期细胞因子风暴对中性粒细胞介导的曲霉抗原的免疫反应和杀伤能力显著减弱,I型IFN(IFN-α和IFN-β)应答降低,T细胞功能受损等造成患者病程中期的免疫状态失衡,加之患者合并影响免疫状态的基础疾病及相关抗炎治疗,这些都增加了IPA的发生风险。所以CAPA的起病时间通常在COVID-19病程中后期。因此,病程中期为CAPA风险期,部分合并高危因素的患者在COVID-19病程中期发病,大部分在病程后期发病。目前关于CAPA诊断时间的相关研究数据提示,其诊断距起病平均时间约为14天,距入ICU 4~13天,少部分院外滞留时间较长者可在入ICU即刻诊断,对于气管插管患者,其诊断时间约在插管后1周左右,总体处于COVID-19病程中后期。这也提示我们,重症COVID-19患者在入ICU之后,似乎还有机会给予预防性的抗真菌治疗,从而降低CAPA的发生风险。而一项关于重症流感患者预防性抗真菌治疗的临床研究最终得到了阴性结果,也可能与IAPA起病时间较早有关。与CAPA相比,IAPA患者病情更重,进展更快,主要体现在SOFA评分更高,氧合指数下降更明显,需要ECMO支持比例更高,并且IAPA血管受侵的发生率更高(50%)。由于流感病毒对气道上皮的溶解作用更明显,所以侵袭性曲霉气管-支气管炎(IATB)更常见(IAPA:>55%;CAPA:20%),而且气道受累更严重。图3 A-E为笔者中心收治的IAPA患者的气管镜下表现,图3F为文献中CAPA患者的气管镜下表现。可以发现:IAPA患者的气道黏膜受累非常广泛,并且非常严重。实际在临床中,COVID-19患者发生IATB也并不少见。上述研究数据可能受限于当时新冠病毒的传染性以及COVID-19患者气管镜检查的次数,但其受累程度及范围确实轻于流感合并IPA患者。
图3 IAPA和CAPA患者气管镜下表现
IAPA与CAPA患者ICU期间并发症的发生率类似,包括呼吸机相关性肺炎(VAP)、导管相关性血流感染(CRBSI)等感染并发症,急性肾损伤(AKI)、休克、肝衰竭、神经系统功能障碍。CAPA凝血功能异常略多见。IAPA与CAPA的病死率均较高。2021年一项单中心回顾性研究表明CAPA和IAPA间的死亡率没有显著差异。笔者团队的研究也发现,尽管IAPA与CAPA疾病严重程度可能有差异,但二者的病死率均接近50%, 约为单纯重症流感或COVID-19的2~3倍。所以, 重症流感和重症COVID-19患者一旦合并了IPA,临床治疗会非常棘手,并且预后较差。IAPA与CAPA的发病率差异不大,但地区差异大。ICU患者IAPA和CAPA真实发生率可能高于10%,欧洲和亚洲甚至达到约20%。但发病率的统计也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BALF采样频率、检测手段的应用(GM实验/PCR)、研究设计、诊断标准选择、纳入患者疾病严重程度、当地抗炎治疗应用情况等。多数IAPA和CAPA均无EORTC/MSGERC中的高危因素。尽管经典高危因素(例如: 器官移植、血液系统/实体器官恶性肿瘤、免疫抑制)比较少, 但仍然非常重要。此外, 还有一些其他非经典高危因素,包括有创机械通气、需要CRRT、脑血管病、需要糖皮质激素或IL-6受体拮抗剂抗炎治疗等。(1)糖皮质激素:目前已经有文献明确证实,糖皮质激素参与流感相关IPA的发病。所以,临床一旦诊断IAPA,应停用糖皮质激素。但对于一些比较特殊的流感合并IPA患者,如后期继发机化性肺炎(OP)或急性纤维素性机化性肺炎(AFOP)者可能还需要加用糖皮质激素治疗。COVID-19的炎症反应非常强烈,对于重症患者,需要积极抗炎治疗。尤其是氧合非常差,甚至需要ECMO支持的患者,更需要强力的抗炎治疗,例如糖皮质激素联合另一种抗炎药物。但目前已有明确的证据证实,无论是糖皮质激素还是托珠单抗,都参与CAPA发病。所以对于CAPA患者,糖皮质激素和托珠单抗能不能使用,也是临床救治的难点。因为这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其可以抑制重要真菌宿主防御系统,抑制IL-6相关免疫应答,降低宿主对曲霉保护性免疫,增加曲霉感染风险;另一方面,其可以通过抑制上皮/内皮/组织损伤而降低IPA的发生风险。临床中合并CAPA后是否需停用抗炎治疗需要综合考虑。(2)抗病毒治疗:有研究建议重症流感尽早使用NAIs,但合并IAPA后怎么办?NAIs为IAPA已知的危险因素,临床如何抉择?其他抗流感病毒药物及抗新冠病毒药物有影响吗?这些都是临床中需要解决的问题。(3)其他预测IAPA/CAPA发病的因素:笔者团队基于本中心的大量数据的分析显示,重症流感患者发生IPA的独立危险因素,包括:激素累积用量高(>200 mg),肺部出现干啰音,顽固性发热(≥3天),CD4+T细胞较低(<200 cell/μl),早期合并AKI需要CRRT治疗,多发结节等,提示此类重症流感患者发生IPA的概率较高。多因素回归分析发现,病情重,实体器官移植患者感染新冠病毒后可能更易出现IPA。所以,CAPA比IAPA具有提示作用的高危因素更少,因此更加强调微生物检测的重要性!GM实验目前在临床中的应用非常广泛。笔者团队研究发现,在非免疫抑制重症流感患者中,GM实验的阳性率比较高,尤其是BALF-GM实验(92%)。第1次的血GM实验阳性率为44%,相对较低,可能由于流感合并曲霉感染达到血管侵袭的阈值需要一定时间。所以如果过早留取血GM实验,可能会出现假阴性的结果。如果连续留取(第3天再留取一次),阳性率可能会与BALF-GM实验相当。因此建议,对于重症流感患者进行血GM检测,需要在1周内相隔3天左右连续进行。两次血GM实验一次阳性诊断效能最佳。BALF-GM无论在病程的早期、还是1周左右的时间,其诊断效能均无明显差异。所以从诊断方面而言,BALF-GM检测并没有时间和连续的要求,但连续监测可能有助于判断真菌负荷及抗真菌药物疗效。笔者团队还开展了常规微生物学检测手段(包括真菌涂片、培养、GM实验)及mNGS在重症COVID-19合并IPA中诊断效能的研究,发现对于早期诊断,BALF-GM实验的敏感性最高(84.9%),血GM最低(40.7%);在诊断准确性方面,BALF-mNGS最优(AUC 0.812)。另外还发现,在现有诊断标准中加入BALF-mNGS,CAPA诊断时间可提前1.5(±2.3)天(P=0.0039)。这也有助于早期开启抗真菌治疗,并且更好地改善患者预后。所以,BALF mNGS是早期诊断的重要补充手段。欧洲一项多中心回顾性研究纳入重症COVID-19和重症流感接受气管插管者,结果表明:BALF-GM在IAPA和CAPA中均有较高的阳性率(70.6% vs. 80%), 血清GM在CAPA中阳性率(50%)远低于BALF-GM,而在IAPA中阳性率较高(76.9%)。所以,血GM可以作为CAPA血管受侵的标志物,一旦出现立即系统抗真菌治疗,并提示预后差。而BALF-GM有助于早期建立IAPA/CAPA诊断。IAPA的CT表现比较典型,早期:在弥漫的磨玻璃影基础上会出现沿气道分布的多发结节/斑片、气道壁增厚、小片实变的表现(图4)。晚期:空洞、空气新月征、大片实变影(图5)。CAPA在病程早期多为非特异性胸部CT表现,外周/双侧/多发磨玻璃影±实变影/小叶内间隔增厚,容易与重症COVID-19本身的影像学表现混淆。病程后期可出现血管受侵型征象,但发生率低;多发结节/空洞较为少见,一旦出现应高度怀疑CAPA(但应除外血栓导致梗死/出血)。影像学在不同人群中价值不同,粒缺患者意义相对较大,尤其是连续监测意义更大,但对CAPA的早期诊断价值偏小,但在其他非经典免疫抑制宿主,尤其是慢性气道疾病、重症流感患者中,CT征象可能有一定的提示。
CAPA可识别的CT征象比IAPA更少。笔者团队的研究数据也表明,重症流感有一些相对特征性的IPA表现,但重症COVID-19基本上没有提示的征象,而且重症COVID-19患者最终出现血管受侵型的征象都比较少,即便出现了血管受侵型征象,时间也相对比较晚,一般在诊断IPA后10天。所以,如果单纯依靠CT诊断CAPA,可能会延误诊断和治疗的时机。
在目前的IAPA和CAPA的诊断标准中,大部分条目都类似(表1)。
2024年发表在《柳叶刀》杂志的一篇综述整合了IAPA和CAPA在诊断和管理流程方面的共同点, 强调了气管镜直视下气道黏膜的表现及通过气管镜获取高质量BALF标本进行病原学检测的重要性。虽然血GM检测阳性率在两者之间存在差异,但血GM仍不失为一种无创且迅速的检测手段。因此,该文章也强调了常规进行血GM检测的重要性。因特异性不高, 未特意提及CT, 但若出现特征性血管受侵征象, 排除其他诊断后, 即使病原学阴性也要考虑拟诊IAPA/CAPA并启动治疗。因此, 尽管IAPA和CAPA在临床特点和发病机制方面存在一些差异, 但二者在诊断和管理流程方面相似之处颇多。对于重症流感患者,早期应用抗病毒药物能够改善预后。NAIs和巴洛沙韦(baloxavir)在对抗流感病毒方面得到广泛应用。但已有明确证据显示,虽然NAIs能够抑制流感病毒复制,但长期使用可能增加曲霉易感性。所以,临床一旦诊断了流感合并IPA,也会考虑换用其他机制的抗流感病毒药物(例如玛巴洛沙韦)。流感病毒尽快转阴才是关键!目前有两类小分子抗新冠病毒药物,主要针对于新冠病毒的两个关键酶,一个是主蛋白酶(Mpro,3CLpro),另一个是RNA依赖的RNA聚合酶(RdRp)。目前无抗新冠病毒药物与CAPA发病关联的研究,但药物相互作用,尤其是3CL蛋白抑制剂与唑类,可能会影响抗真菌治疗效果。三唑类药物是抗曲霉治疗的一线用药,两性霉素B类是二线用药,棘白菌素类药物不良反应小,但对于IPA而言,其地位仅为挽救治疗或挽救联合治疗(表2)。研究发现,与IAPA相比,在CAPA治疗中伏立康唑浓度达标时间更晚(5天后达标比例更多),谷浓度偏低。这可能由于糖皮质激素与抗新冠病毒药物间的相互作用导致。治疗IAPA和CAPA过程中,抗炎药物与抗病毒药物是必须应用的,所以在联用时,一定要注意进行药物监测,必要时可以考虑换用新型三唑类药物或其他抗病毒药物,尽量减少药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入ICU后应用系统性糖皮质激素已明确为IAPA的高危因素。但诊断流感后停用糖皮质激素的策略一定对吗?以下述病例为例:病例1:65岁女性,既往体健;活动后呼吸困难7天,加重5天,于2023年3月8日入院,入院后发热,氧合指数130 mmHg。血常规:WBC 7.24×109/L,NEU 6.42×109/L,LYM 0.55×109/L,CRP 95.21 mg/L,PCT<0.02 ng/ml。BALF NGS:甲型流感病毒(序列数28947),烟曲霉(序列数26),肺炎链球菌(序列数78);新甲型H1N1流感病毒核酸阳性。诊断:IAPA。予以哌拉西林他唑巴坦+奥司他韦+伏立康唑抗感染治疗。目标抗感染治疗后患者病情持续恶化,氧合进行性下降,影像学提示右肺出现实变影(图7)。呼吸支持策略由NPPV过渡为IPPV仍无法维持,最终启动ECMO。IPPV及VV-ECMO当日于右下后基底段冷冻肺活检,病理提示:肺泡间隔增宽,间质纤维母细胞增生,可见Masson小体,伴淋巴细胞为主的慢性炎细胞浸润,部分肺泡上皮增生,肺泡腔内可见吞噬细胞聚集。特殊染色:PAS(-),银染(-),抗酸(-),Masson(+)。最终诊断:继发性机化性肺炎;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重症流感病毒性肺炎;侵袭性支气管-肺曲霉菌病。治疗予甲强龙320 mg qd×3天→80 mg×5天→40 mg×14天。后患者氧合及影像学均明显好转,顺利撤除VV-ECMO及有创机械通气。对于该患者,流感和IPA的诊断都非常明确。尽管大剂量激素在重症流感及IAPA中均有害,但该患者在针对性抗感染基础上影像学仍然在进展,病理也提示当下的主要问题不是感染,而是继发的机化性肺炎。所以我们加用了激素。由此可见,对于重症流感合并IPA的患者,究竟要不要应用糖皮质激素,仍需要根据当前主要矛盾及疾病所处时期综合判断。大部分患者如果没有继发肺损伤或机化性肺炎,停用激素可能有助于控制真菌感染。但如果患者感染之后继发肺损伤或机化性肺炎,仍然需要抗炎治疗来改善氧合。病例2:44岁女性,既往体健,长期化学性物质(油漆)接触史;2023年12月8日起病,外院诊断“甲流(H3N2)合并烟曲霉”,12月17日起予美罗培南+伏立康唑+奥司他韦抗感染,持续发热(Tmax>38℃),呼吸困难加重,影像学进展,双肺弥漫的沿气道分布的结节和斑片影,气道明显增厚。12月20日入我院MICU。12月21日复查病原学:BALF甲型流感病毒核酸阳性(CT值32.25);细菌涂片未及细菌;细菌培养结果为木糖氧化无色杆菌(<1×103 cfu/ml);真菌涂片找到真菌菌丝;真菌培养结果为烟曲霉;BALF-GM检测8.28;血GM检测1.12。监测伏立康唑浓度:2.4 ng/ml。伏立康唑敏感/浓度达标,但疗程不足,继续伏立康唑200 mg q12h抗真菌治疗,加用两性霉素B 10 mg q12h雾化。12月22日出现休克。血常规:WBC 34.55×109/L,NEU 33.16×109/L。炎症指标:CRP>160 mg/L,PCT<0.2 ng/ml,IL-6 293.38 pg/ml(<5.4);BALF NGS回报:H3N2流感病毒,烟曲霉。考虑为真菌所致感染中毒性休克。未调整抗感染方案,予液体复苏及氢化可的松0.2 g qd×5天抗炎后纠正。尽管该患者为IAPA,但同时合并了严重的感染中毒性休克,所以也加用了糖皮质激素。此外,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出现了持续的气道痉挛及严重的呼吸性酸中毒,气道峰压报警,二氧化碳潴留非常明显,pH<7.0,PaCO2 126 mmHg(图8)。予吸入糖皮质激素(ICS))联合长效β2受体激动剂(LABA)及长效抗胆碱能药物(LAMA)q4h雾化,间断加用沙丁胺醇喷雾;减少一切气道刺激,包括停止气管镜吸痰,停止两性霉素B雾化及镜下给药,仅保留俯卧位4 h qd加强痰液引流(镇静镇痛)。但患者气道峰压最高仍可高达45 mmHg,大部分波动于29~35 mmHg,呼气气流持续受限。因患者总IgE轻度增高,且气道高反应明显,因此加用了甲强龙40 mg qd×5天,后患者气道痉挛有所好转,但痰液增多,继发碳青霉烯类耐药铜绿假单胞菌(CRPA)感染,被迫停止糖皮质激素治疗。后续患者因难以纠正的严重呼吸性酸中毒,启动VV-ECMO,但最终因脑出血放弃。此患者气道炎症反应严重,高反应明显。值得我们反思的是:如果早期及时加用系统性糖皮质激素抑制气道高反应,而非后期院感风险增加后再考虑应用,能否改变患者结局。目前已经基本确认激素是CAPA的危险因素。但COVID-19患者往往具有强烈的全身炎症反应,所以此类患者合并IPA,抗炎药物是否停用,也是临床面临的难题。以下述病例为例。病例3:58岁女性,高血压、慢性支气管炎病史,发热伴咳嗽9天,加重2天。2022年12月19日入ICU,12月13日咽拭子新冠抗原(+),12月17日痰新冠核酸(+),12月20日BALF mNGS:新冠病毒(序列数27130),烟曲霉(序列数89),BALF-GM 7。入院后给予经口气管插管及机械通气。血气分析(PEEP 12 cmH2O,FiO2 1.0):pH 7.396,PaCO2 38.5 mmHg,PaO2 68.9 mmHg。入院前CT提示单肺受累,沿气道分布的斑片和结节影(图9)。经过抗病毒和抗真菌治疗后感染指标和炎症指标均明显改善,6天后复测BALF GM 1.2,较前明显下降(图10)。患者曲霉感染得到控制,但氧合改善不理想,无法脱机。12月26日患者氧合指数一度降至100~120 mmHg,复查胸部CT提示沿气道分布的结节和斑片影基本消失,但新发弥漫磨玻璃影(图11)。考虑与新冠病毒所致炎症反应引发的肺损伤有关。复查炎症指标,Fet 1600 μg/L,IL-6 244 pg/ml(<5.4)均明显升高。在继续抗真菌治疗的前提下,加用甲强龙80 mg qd×10天抑制炎症反应及肺损伤。患者氧合及胸部影像学明显好转,最终顺利脱机拔管。治疗方案的制定要个体化评估宿主、综合考虑病原(病毒/真菌)以及宿主的炎症反应和免疫状态,针对各个环节采取干预措施。药物的联合应用可能对一个因素有益,对另一因素产生风险,但总体目标是:阻断疾病进程,降低严重程度及病死率(防止疾病进展,由气道侵袭进展为血管侵袭)。重症COVID-19与重症流感的炎症反应有所区别:COVID-19及流感细胞因子峰值水平相似,但COVID-19细胞因子高水平持续时间明显延长;COVID-19发病至重型/危重型约为9天,是流感发病至转为重症时间的2倍;重症COVID-19炎症反应可持续,可反复,整个病程中可能涉及多轮抗炎。评估患者每一时期主要矛盾(炎症反应、免疫状态及合并感染情况)至关重要,目前还没有生物标志气物(包括细胞因子)可指导免疫治疗,大多数仍基于临床指标。所以临床中会将患者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存在过度炎症反应而无感染的患者,这部分患者最可能受益于抗炎治疗(抗细胞因子生物制剂,如抗IL-1/抗IL-6生物制剂),将减少组织损伤,但感染风险增加。另一类是存在免疫瘫痪或感染严重的患者,此类患者可以辅助刺激免疫治疗(如重组干扰素γ)可能有益,但应警惕过度刺激造成炎症反应反复。个体化免疫治疗应是未来重要的研究方向,是在抗病毒治疗、抗真菌治疗基础上改善IAPA/CAPA患者预后的重要手段。流感病毒和新冠病毒在致病机制方面存在差异——流感病毒组织损伤更重,更早突破血管受侵阈值。与CAPA相比,IAPA起病更急、病情更重;气道损伤更重,IATB更常见且更严重;血管受侵型更常见;血GM阳性率较CAPA高;CT可识别征象较CAPA多;NAIs本身可作为高危因素之一,应用时应权衡利弊;治疗过程中药物相互作用/抗炎治疗涉及较CAPA相对少;预防性抗真菌治疗可能因起病早(入ICU时间短)而失败。尽管IAPA与CAPA存在上述差异,但总体而言二者非常相似,严格区分的意义不大。二者临床诊断和治疗的原则都是强调“早诊早治”。除了早期规范治疗(抗病毒/抗真菌/抗炎)外,还需严格把握个体化抗炎治疗的时机,避免感染加重,以及炎症反应造成的脏器损伤。动态监测不同时期患者感染、免疫状态、脏器损伤的矛盾变化,找准干预时机,对于IAPA与CAPA,也是重要的干预手段。 [1] Dewi IM, Janssen NA, Rosati D, et al. Invasive pulmonary aspergillosis associated with viral pneumonitis[J]. Curr Opin Microbiol, 2021, 62:21-27. [2] Bartoletti M, Pascale R, Cricca M, et al. Epidemiology of Invasive Pulmonary Aspergillosis Among Intubated Patients With COVID-19: A Prospective Study[J]. Clin Infect Dis, 2021, 73(11):e3606-e3614. [3] Feys S, Almyroudi MP, Braspenning R, et al. A Visual and Comprehensive Review on COVID-19-Associated Pulmonary Aspergillosis (CAPA)[J]. J Fungi (Basel), 2021, 7(12):1067. [4] Verweij PE, Brüggemann RJM, Azoulay E, et al. Taskforce report on the diagnosis and clinical management of COVID-19 associated pulmonary aspergillosis[J]. Intensive Care Med, 2021, 47(8):819-834. [5] Reizine F, Pinceaux K, Lederlin M, et al. Influenza-and COVID-19-Associated Pulmonary Aspergillosis: Are the Pictures Different?[J]. J Fungi (Basel), 2021, 7(5):388. [6] Lu LY, Lee HM, Burke A, et al. Prevalence, Risk Factors, Clinical Features, and Outcome of Influenza-Associated Pulmonary Aspergillosis in Critically Ill Patients: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J]. Chest, 2024, 165(3):540-558. [7] Gioia F, Walti LN, Orchanian-Cheff A, et al. Risk factors for COVID-19-associated pulmonary aspergillosis: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J]. Lancet Respir Med, 2024, 12(3):207-216.[8] Huang L, Zhang Y, Hua L, et al. Diagnostic value of galactomannan test in non-immunocompromised critically ill patients with influenza-associated aspergillosis: data from three consecutive influenza seasons[J]. Eur J Clin Microbiol Infect Dis, 2021, 40(9):1899-1907. [9] Rouzé A, Lemaitre E, Martin-Loeches I, et al. Invasive pulmonary aspergillosis among intubated patients with SARS-CoV-2 or influenza pneumonia: a European multicenter comparative cohort study[J]. Crit Care, 2022, 26(1):11. [10] Park SY, Lim C, Lee SO, et al. Computed tomography findings in invasive pulmonary aspergillosis in non-neutropenic transplant recipients and neutropenic patients, and their prognostic value[J]. J Infect, 2011, 63(6):447-456.[11] Koehler P, Bassetti M, Chakrabarti A, et al. Defining and managing COVID-19-associated pulmonary aspergillosis: the 2020 ECMM/ISHAM consensus criteria for research and clinical guidance[J]. Lancet Infect Dis, 2021, 21(6):e149-e162.[12] Verweij PE, Rijnders BJA, Brüggemann RJM, et al. Review of influenza-associated pulmonary aspergillosis in ICU patients and proposal for a case definition: an expert opinion[J]. Intensive Care Med, 2020, 46(8):1524-1535.
[1] Dewi IM, Janssen NA, Rosati D, et al. Invasive pulmonary aspergillosis associated with viral pneumonitis[J]. Curr Opin Microbiol, 2021, 62:21-27. [2] Bartoletti M, Pascale R, Cricca M, et al. Epidemiology of Invasive Pulmonary Aspergillosis Among Intubated Patients With COVID-19: A Prospective Study[J]. Clin Infect Dis, 2021, 73(11):e3606-e3614. [3] Feys S, Almyroudi MP, Braspenning R, et al. A Visual and Comprehensive Review on COVID-19-Associated Pulmonary Aspergillosis (CAPA)[J]. J Fungi (Basel), 2021, 7(12):1067. [4] Verweij PE, Brüggemann RJM, Azoulay E, et al. Taskforce report on the diagnosis and clinical management of COVID-19 associated pulmonary aspergillosis[J]. Intensive Care Med, 2021, 47(8):819-834. [5] Reizine F, Pinceaux K, Lederlin M, et al. Influenza-and COVID-19-Associated Pulmonary Aspergillosis: Are the Pictures Different?[J]. J Fungi (Basel), 2021, 7(5):388. [6] Lu LY, Lee HM, Burke A, et al. Prevalence, Risk Factors, Clinical Features, and Outcome of Influenza-Associated Pulmonary Aspergillosis in Critically Ill Patients: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J]. Chest, 2024, 165(3):540-558. [7] Gioia F, Walti LN, Orchanian-Cheff A, et al. Risk factors for COVID-19-associated pulmonary aspergillosis: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J]. Lancet Respir Med, 2024, 12(3):207-216.[8] Huang L, Zhang Y, Hua L, et al. Diagnostic value of galactomannan test in non-immunocompromised critically ill patients with influenza-associated aspergillosis: data from three consecutive influenza seasons[J]. Eur J Clin Microbiol Infect Dis, 2021, 40(9):1899-1907. [9] Rouzé A, Lemaitre E, Martin-Loeches I, et al. Invasive pulmonary aspergillosis among intubated patients with SARS-CoV-2 or influenza pneumonia: a European multicenter comparative cohort study[J]. Crit Care, 2022, 26(1):11. [10] Park SY, Lim C, Lee SO, et al. Computed tomography findings in invasive pulmonary aspergillosis in non-neutropenic transplant recipients and neutropenic patients, and their prognostic value[J]. J Infect, 2011, 63(6):447-456.[11] Koehler P, Bassetti M, Chakrabarti A, et al. Defining and managing COVID-19-associated pulmonary aspergillosis: the 2020 ECMM/ISHAM consensus criteria for research and clinical guidance[J]. Lancet Infect Dis, 2021, 21(6):e149-e162.[12] Verweij PE, Rijnders BJA, Brüggemann RJM, et al. Review of influenza-associated pulmonary aspergillosis in ICU patients and proposal for a case definition: an expert opinion[J]. Intensive Care Med, 2020, 46(8):1524-1535. 黄琳娜
中日友好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治医师,医疗组长;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认证的PCCM专科医师,中国医师协会呼吸医师分会危重症学组青年委员;以第一作者及通讯作者发表SCI论文10篇,中文核心期刊论文多篇;作为子课题负责人参与中国医学科学院项目1项,作为项目骨干参与多项国家级及省部级课题;作为中日友好医院呼吸危重症救治与创新团队主要成员,获得全国创新争先奖牌。
 后可发表评论
后可发表评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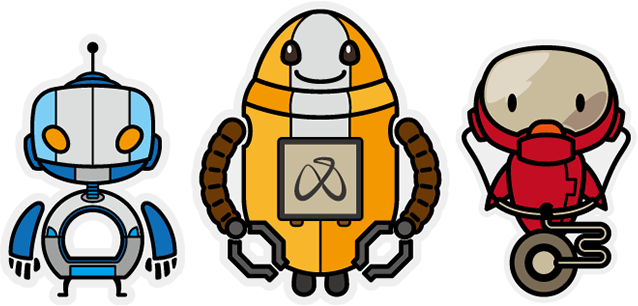
 公众号
公众号
 客服微信
客服微信